龍門陣里的成都“新響”:從火鍋之城到科幻之都
說起成都,你會想到什么?
美景、美女、美食、熊貓、麻將、茶館、三星堆、春熙路、雙流兔頭……一個最宜居的“網紅老城”或許早已深深扎根在你的腦海。但這遠遠不夠,一個“科幻之都”的名號,就足以改變你對這座城市固有的“偏見”。
圖/視覺中國
正如原四川省科普作家協會理事長、首屆中國科幻銀河獎得主吳顯奎所言,“四川是中國地理上的洼地,但卻是中國科幻的高地”。高地上聳立的最高峰,當屬成都無疑。時至今日,它依然在以驚人的速度崛起。
那么,一座地處西南內陸,被大山包圍的古老之都,是如何成為“中國最科幻城市”的呢?
土壤
環蜀皆山也。
橫斷山脈、大巴山脈、巫山、大婁山,四面合圍,將這方盆地小心地攏住,阻斷了冬天橫肆的寒流與季風,令四川比同緯度的江南更早感知到春天。
地處龍門山和龍泉山之間的成都平原,更是占盡地利,溫潤的氣候、豐饒的物產,讓這里自古以來便獲得了“天府之國”的美譽。十年前的秋天,當山東人孫悅從草木搖落的故鄉來到溫暖依舊的蓉城,映入眼簾的滿園桂花令他記憶猶新。
蜀江水碧蜀山清,“巴適”,是寫在成都人基因里的,它氤氳在茶碗里,散落在牌桌上,沸騰在火鍋和串串的紅湯里,回響在街頭巷尾的“龍門陣”里。在成都讀了三年大學的河南人王喆笑言,成都人喜歡去喜茶排隊,但他們是為了買奶茶么?不,他們是為了擺龍門陣。
圖/視覺中國(成都街頭)
是的,成都人愛扎堆。土生土長的成都人周覃回憶說,小時候父親帶他去買菜,回來的路上看到人家在街邊斗地主,“那腳就挪不動了”,結果“龍門陣”擺了一個多小時,回到家時路燈都亮了起來,父子倆為此遭到了母親一通數落,“可我媽也這樣,一次她下樓遛狗,只顧著和別人說話,最后狗跑丟了。”
成都是一座來了就不想離開的城市。
上世紀90年代,從小就生活在新疆的楊楓回到了自己戶籍上的故鄉。見慣了邊疆風物的她一時難以適應成都狹窄的街道和陰雨連綿的天氣,她把行李箱放在陽臺上,對父親說:“箱子我不打開,半年時間,能適應我就留下來,適應不了我直接回新疆。”結果,這一留就是二十多年,楊楓在成都安了家,女兒如今在讀大學,往后余生,她將與這座城市時刻牽連。
閑適的生活和暢談,為想象力的生長留出了充足空間。
周覃自稱腦子里裝著無數千奇百怪的故事,大都是從大人們日常閑聊中聽來的。在成都的二十多年里,出身文學世家的楊楓一直在與文字打交道,中間有十多年在《科幻世界》擔任編輯,在她看來,成都能夠成為中國科幻氛圍最濃厚的城市,有著人文上的天然基因,“當你遠離都市的喧囂,節奏慢下來,仰望的星空才會更加純粹”。
從三星堆到古金沙再到開明氏,“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相比中原,這里的文化自成一脈,更多涂上了夏商時期幻想和浪漫的色彩。盡管隨著秦帝國鐵騎踏破山缺,古蜀最終匯入華夏,但在“子曰”之外,古蜀文明卻一直連綿不衰。
放眼全世界,除了在成都,你還能看到帝王陵墓隱藏在臣子祠堂中的“奇觀”么?“諸葛亮多智而近妖”,在武侯祠背后,是成都人對智慧和想象的崇拜。《科幻世界》主編拉茲認為,科幻之所以能在成都生根并枝繁葉茂,恰恰是古蜀文明在今日發出的“新響”。
悠久的文化和歷史上幾次大規模移民,共同塑造了成都人“外表溫和,開放包容”的性格。當歷史的腳步漸行漸遠,這種性格依舊體現在方方面面。
拉茲有時候會感到很不可思議,成都作為一個地處西南的內陸城市,竟然會成為中國的“漢服之城”,街上的姑娘們早已將其當成了日常穿著。當《科幻世界》的編輯們穿著漢服和蘿莉裝一起走進位于四川科協的辦公區,便是這座終日嚴肅的大樓難得露出笑容的時刻。
圖/視覺中國
2007年,成都國際科幻/奇幻大會舉辦期間,在《科幻世界》工作的楊楓陪同外國友人一起逛寬窄巷子、吃串串、坐茶館……成都人展現出的開放胸襟和對賓客發自內心的歡迎令她這位“異鄉人”第一次從心底對這座城生出了認同,“我想我就算個成都人了吧,感覺挺自豪的”。
拉茲說,成都市政府從來不會把科幻當成舶來品,也不會生硬地將一種藝術形式與科學技術關聯。他回憶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現任四川副省長羅強還給《科幻世界》供過稿子。但是,對科幻的支持并非基于領導個人喜好,“主要還是面向未來的一種包容開放的態度”。
基于此,不僅以地方政府和省科協為代表的機關單位經常牽頭舉辦與科幻相關的活動,還提出將在成都建設“中國科幻城”項目。2020年5月,“第五屆中國(成都)國際科幻大會”作為成都重大文創品牌活動,被寫入成都市政府報告中。
如果沒有《科幻世界》,我們還能不能看到劉慈欣?還能不能看到《流浪地球》?成都還能不能成為“科幻之都”?周覃說,這是每個科幻迷都不敢設想的問題。
根據地
如果將中國“新時期”科幻文學至今四十多年歷程梳理一個脈絡,那么《科幻世界》必然占據著中軸線。
圖/科幻世界微博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在京召開,閉幕式上,郭沫若宣告,“科學的春天到來了”。會后,在相關政策要求下,各地科協紛紛創辦刊物,《科幻世界》的前身《科學文藝》便應運而生。
1984年,楊瀟開始擔任《科學文藝》主編時,雜志社的賬上只有6.3萬元,每年還有幾十萬虧空。1990年,楊瀟決定在成都申請舉辦世界科幻協會年會,在沖破了國內輿論的重重阻力后,這個瘦女人坐了七天七夜火車,最終在海牙年會上擊敗波蘭,獲得了舉辦權。
后來,隨著舉辦1997年度世界科幻大會以及布局圖書出版等業務,影響越來越大的同時,《科幻世界》也逐漸走出危機。尤其是1999年的高考作文“撞車”事件,更是令其一度“出圈”。
在當年高考前一周,《科幻世界》第七期刊登了時任社長阿來的文章,講述記憶移植實現人類長生不老的夢想。而當考生們拿到全國高考語文卷時,竟然發現作文題正是《假如記憶可以移植》,此事當時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科幻熱潮。
作為中國科幻的根據地,《科幻世界》一直在向文壇源源不斷地輸送活水。拉茲說,無論中國科幻處于低谷還是高峰,《科幻世界》一直將培養作家和生產內容作為核心使命。
今天,不僅并稱為中國科幻“四大天王”的何夕、劉慈欣、王晉康和韓松均在《科幻世界》上開始創作生涯,諸如阿缺和陳勁波等新生代科幻作家也在《科幻世界》提供的舞臺上成長起來。
不僅如此,1986年和2010年,《科幻世界》及相關人士先后組織創辦“銀河獎”和“星云獎”,對科幻作家的號召力進一步加強。不過,在拉茲看來,設立獎項的目的不是頒獎,而是為了撮合作家們在現實中“聚一下”“開開腦洞”,能給科幻迷們靜下心來平等交流的機會,“在生活中,他們是很難找到同路人的”。
許多人都說,正是因為《科幻世界》的存在,中國科幻迷才能凝聚起來。
正在擔任四川大學科幻協會會長的大三學生王喆經常會問新會員一個問題,“你說你是科幻迷,那你有什么最想做的事情嗎?”當他聽到“我想去《科幻世界》看看”此類的答案時,總會感同身受。
王喆從高中時期就開始訂閱《科幻世界》,可是自己閱讀的快感卻無從分享,“偶爾也會有人找我借書看,可最多也就有三四個人能和我討論科幻故事”。孫悅也擔任過川大幻協會長,他說,中國的科幻文化是小眾的,圈子是割裂的,每個科幻迷都體會過孤獨感。
2010年,孫悅違背了家人的意愿選擇到四川讀大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成都的科幻氛圍很好”。相同的目的吸引著王喆,當他身處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中間、大家可以靈活地“拋梗接梗”時,他感覺自己找到了歸屬,“我終于不再是一個人了”。
當前,中國科幻城還在規劃中,相關科幻企業也分布在成都各地,拉茲說,如果成都科幻有一個地標的話,“那就是我們《科幻世界》了”。隨著科幻在中國的大火,《科幻世界》每年都會接待幾千名來訪者,他們都是諸如孫悅和王喆等科幻迷。
拉茲說,(人們來參觀)會形成一種正向的激勵,尤其是愛好科幻的學生們,當他們走出校園,大多也會出于對科幻的熱愛和成都濃厚的科幻氛圍而選擇留下來。
薪火
談及當前中國科幻蓬勃發展的局面,拉茲感慨說:“(因為)科幻迷們長大了。”
作為《科幻世界》的忠實讀者以及1999年高考作文“撞車”事件受益者,郭帆和龔格爾在二十年后聯手制作了《流浪地球》,中國科幻電影也由此迎來元年。
可長大的不只是他們。2011年,孫悅當選川大科幻協會會長,當年便帶領會員們以志愿者的身份全程參與了第二屆“星云獎”活動。2013年,他開始在“星云獎”官方網站“科幻星云網”兼職運營工作。臨近畢業時,出于對科幻的熱愛,他放棄政府公職,受朋友之邀,正式加入“科幻星云網”,旨在打造一個粉絲聚集和作家孵化的平臺。
圖/視覺中國
2016年,孫悅又與朋友一起創辦了“賽凡科幻空間”。“賽凡”便是“SCIFI”——科幻的諧音,作為國內第一個科幻主題空間,他們得到了成都網信辦等相關部門的支持。2016年,賽凡開始主辦“未來科幻大師獎”。
發展至今,賽凡不僅擁有線下實體空間和線上網站及網店,更是會進行科幻原創IP周邊產品的開發。2018年,當《流浪地球》還處于S級保密期間,在市面上沒有任何物料流通的情況下,賽凡便為這部電影做了整套周邊衍生產品的圖庫和風格設計指南。
創辦“八光分文化”的楊楓更是直接從《科幻世界》走出的創業者。2003年,楊楓想到要為自己尋找“一條新路”,便果斷放棄了出版社編制內的“鐵飯碗”,選擇加入《科幻世界》做了一名普通的編輯。此后十余年里,有無數篇科幻作品經由楊楓之手與讀者見面。
可是,到了2016年,楊楓那顆不安分的心再次躁動起來,“我不知道未來要做什么,但我知道首先要出來”。從《科幻世界》離職后,她得到了一位投資人的支持,一個月后便創立了“八光分文化”。
“八光分”一詞也有著特殊的含義,它代表陽光到達地球的距離,這是孕育生命的距離。公司創立之初,只有楊楓一人,后續隨著業務的拓展,來自國內外的各種文化背景的年輕人紛紛加入,楊楓說,“我就像是一個組盤的,將藏在各個緯度的科幻愛好者吸納進來。”正如《科幻世界》一樣,今天的八光分也搭建了一個“舞臺”,真正“唱戲”的是那些對科幻癡迷的人。
八光分的業務范圍主要集中在圖書出版、培養原創作家和科幻IP影視化等方面,成立至今,不僅出版了曾獲得第九屆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最佳非虛構作品金獎和第29屆科幻銀河獎最佳相關圖書獎的《追夢人——四川科幻口述史》、與英國BBC廣播公司合作出版了《神秘博士》系列中文圖書,還與相關機構共同發起了冷湖科幻文學獎。
圖/八光分里一臺偽裝成電話亭的 “時光穿梭機”TARDIS
此前,八光分曾做過一個統計,發現除了最老牌的《科幻世界》,近年在成都已經誕生了將近二十家與科幻相關的新興機構,覆蓋圖書出版、獎項運營、科幻周邊、影視漫畫開發等多個領域,產業鏈條已經初步搭成。
正是因為濃厚的科幻氛圍以及科幻薪火的傳承,成都才得以在2019年超越北京和深圳,成為“中國最科幻城市”,并將代表中國角逐“2023年世界科幻大會”的主辦權。楊楓說,在成都“申幻”的路上,自己和八光分將“不遺余力地搖旗吶喊”。
但是,繁盛之下也有隱憂。拉茲說,中國科幻創作今天已經進入歷史上最繁榮的時期,但是在出版之外,其他相關產業并沒有出現突破性進展,“比如影視除了《流浪地球》并沒有其他好作品出來”。
在他看來,成都要想成為真正的“科幻之都”,后續還需要實現資源整合,在相關政策引導下更好地完善產業鏈。而孫悅等創業者則呼吁能夠在稅收等方面給予創業公司具體的支持。
拉茲說,當前中國科幻界還存在人才缺乏的現象,“并不是沒有,而是難以找到,可能某些人在企業或高校從事其他工作,他們對科幻有著專業技能或深刻見解,但科幻界卻不知道他們的存在,(原因是)缺少一個能夠實現跨界的平臺”。
事實上,接下來將要接過火把的人正在默默準備著。就讀高分子材料專業的王喆雖然現在沒有想好畢業后具體從事什么,但科幻的種子早已在心里深深埋下。
等到種子發芽的那一天,王喆說,他會成為一名研究者和觀察者,在更宏觀的層面把握科幻產業的發展。
或許正是他,能夠完成拉茲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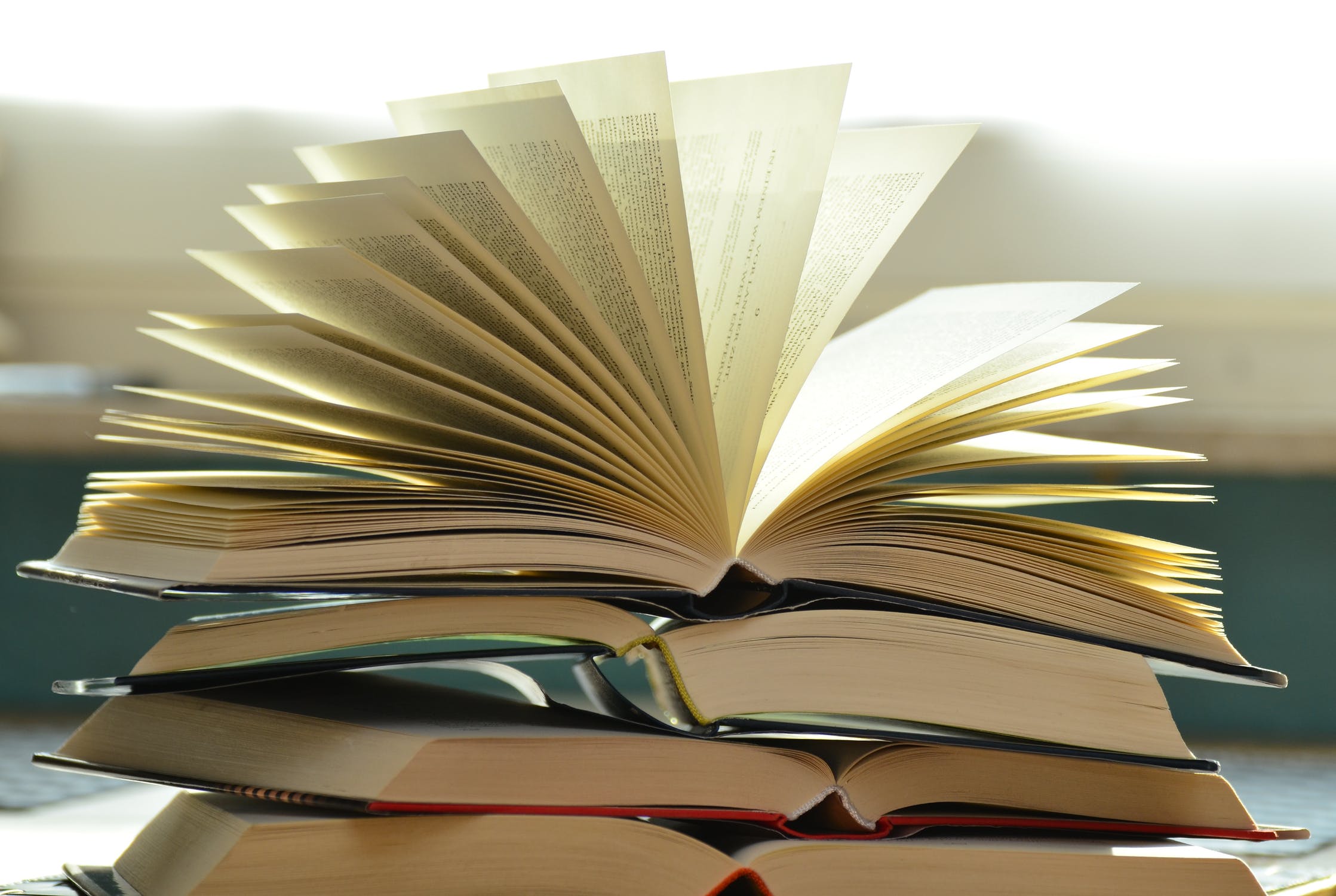
 AI財經社
AI財經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