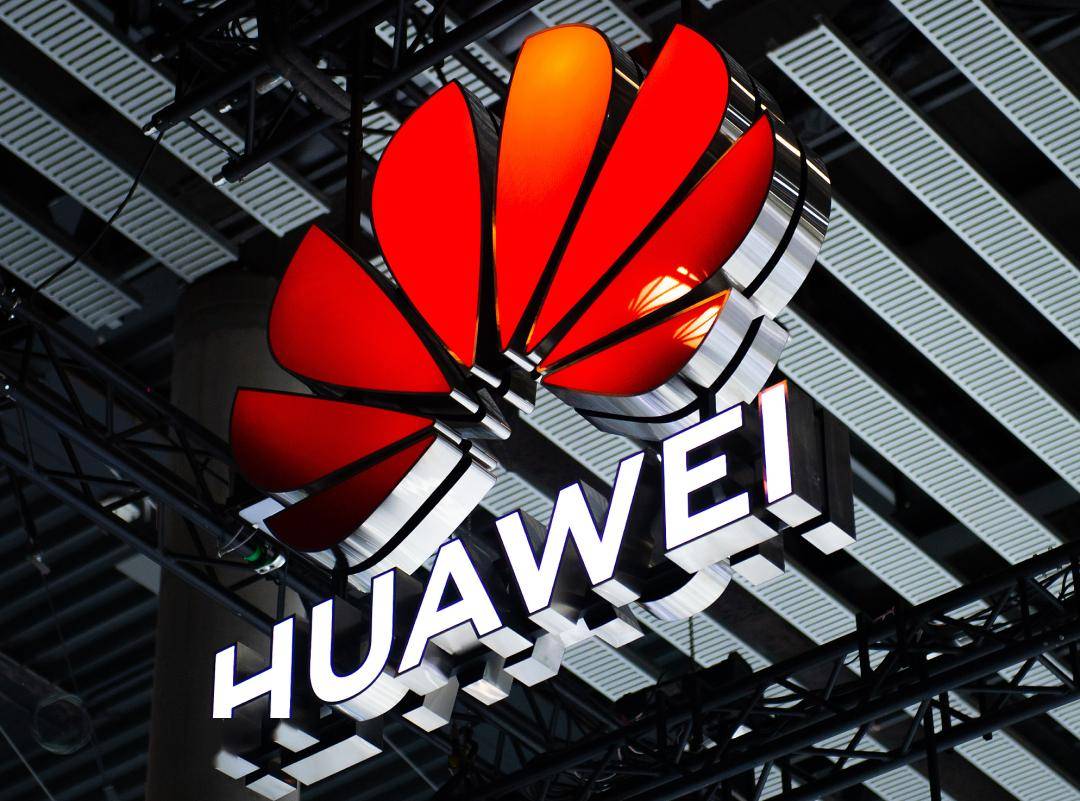華為哈勃化身硬科技IPO收割機
“哈勃投資是華為遭美國制裁背景下專門成立的。”
2020年華為全聯接大會上,輪值董事長郭平向外界表示了華為哈勃成立的初心。當時華為哈勃成立僅有半年,還是個年輕的VC。哈勃誕生之初并不被外界看好,畢竟誕生的背景有些悲壯色彩,而且還違反了任正非的三不原則,即不碰數據、不做應用,不做股權投資。
哈勃一直伴隨爭議,這也同樣表示哈勃注定是VC圈里不一樣的新物種。
2019年9月,華為哈勃成立五個月時出手投資了思瑞普,此次投資又打破了華為內部不投供應商的規定。根據思瑞浦的招股書顯示,華為是其最大客戶占總營收的57%,此次投資后,華為哈勃成為了思瑞浦的第六大股東。
剛開始,哈勃投資的動作并不密集,出手也較為謹慎,前半年只投資了兩家公司。但隨后哈勃出手的頻率越快越快,距今已投資超80家企業。
隨著頻繁投資,業內人士也曾表示,看不懂華為哈勃投資是為了產業還是財務回報。哈勃也確實有突擊入股的事情,意在財務回報的傾向。但實際上,仔細研究哈勃的投資脈絡不難發現,哈勃的投資思路逐漸清晰,基于半導體產業,向上游企業挖掘被投標的。
如今,這個年輕的VC的投資布局清晰可見,并且已經來到了收獲期。

據獵云網了解,目前華為哈勃已收獲8個IPO,其中思瑞浦解禁期剛過,哈勃便拋售股票套現近1個億。此外,還有4家正在IPO流程階段,一旦上市華為下半年又將收獲一批IPO。
隨著被投企業的快速成長,當下的收獲期或許只是哈勃的“前菜”。
華為老兵牽頭,哈勃向產業上游走
在成立哈勃之前,華為的投資一直十分低調。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從 2006 年到 2019 年, 13 年間華為公開的投資并購事件只有 14 筆。一直靠自研技術的華為,對待投資的態度比較保守。根據消息稱,華為內部的投資由二級部門企業發展部推進,雖然企業發展部分管并購、投資,但是真正拍板決定的由常務董事會決策。所以在華為內部,該部門的份量并不重,績效考核不包括投資回報一項。
企業發展部總裁自2018年起由白熠擔任,他也是哈勃投資的董事長。如今已在華為工作超20年,先后在華為企業發展部、金融風險控制中心等任職。
前十幾年一直保守投資的華為,卻在2019年大張旗鼓的進軍VC。這背后離不開市場的變化。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表示,在美國的制裁下,專門成立了哈勃投資,通過投資和華為的技術去幫助整個產業鏈。
在芯片受制裁之前,華為海思一直采用的是Fabless模式,即負責芯片的電路設計與銷售,生產、測試、封裝等環節則外包。所以制裁后,芯片設計、芯片制造、芯片封裝和測試等多個產業鏈環節需要華為自己研究摸索。
制裁后需要自研技術也凸顯了另一個現實,國內急需一條可替代的國產芯片產業鏈,這也是華為哈勃誕生的最大任務。
從哈勃投資的領域來看,首先華為計劃自建晶圓廠,因此投資領域主要是圍繞晶圓廠所涉及的產業。例如半導體材料、制造、封裝測試等。除晶圓廠所涉及的游shan產業之外,在第三代半導體企業方面,哈勃的布局也較為密集,投資了天科合達、天岳先進等。從投資風格來看,華為哈勃并不“害怕”風險,在被投企業中不乏風險性高成立較晚的企業。芯片行業的初創項目,本身就具備極大的不確定性,而被投企業立芯軟件和阿卡思微電子都2020年才成立的新公司。

(注:圖表信息截至2022年4月)
值得注意的是,在向半導體行業上游不斷深耕的背后,華為哈勃的投資鮮有和海思芯片處于同一個賽道的高端芯片類企業,這也是華為哈勃在半導體產業投資的唯一一條界限。
目前來看,華為哈勃的近幾次投資賽道落在了汽車產業和新能源電池上,例如汽車芯片廠商旗芯微,新能源企業衛藍新能源等。結合華為自身在新能源汽車的布局來看,未來哈勃的投資賽道可能不止局限在半導體相關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的上游公司同樣有機會攜手華為。

(注:圖表信息截至2022年2月)
給錢給訂單,一路扶到科創板
打破不投資供應商的規定后,哈勃扶持被投企業的動作不僅僅體現在資金方面,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已上市的被投企業招股書中看出。
2012年思瑞浦成立,自2016年起在模擬芯片賽道發力,2019年7月哈勃7200萬投資了思瑞浦,為后者的第六大股東,持股8%。此次投資之前,思瑞浦便是華為的供應商,為5G基站供應信號鏈芯片。2018年華為給思瑞浦貢獻的收入僅為170萬元,占其總營收的1.5%
雖然是供應商,但是在華為投資之前,思瑞浦的生活并不光鮮亮麗,作為一家小型模擬芯片廠商,2018年,思瑞浦收入1.14億元,虧損882萬元。就在2019年哈勃入股后,根據招股書顯示,2019年思瑞浦收入增長167%達到3.04億元,凈利潤暴漲至7098萬元。這其中2019年華為貢獻的收入達到1.7億元,占總營收的57.13%。
給了資金扶持之后又給訂單,華為哈勃算是一路給思瑞浦扶到了科創板。
思瑞浦也并沒有讓華為哈勃失望,2019年完成華為哈勃的融資后,思瑞浦的估值為9億元。一年后思瑞浦在科創板上市后,市值達450億元。按照比例計算,此時哈勃的持股市值超過26億元。上市解禁期剛過,華為哈勃減持約16萬股,套現規模約9000萬元。兩年華為哈勃的投資回報超25倍。
從小型企業扶持至上市公司,思瑞浦并不是唯一一家。
2021年11月做陶瓷波導濾波器的燦勤科技登陸科創板,它的主要產品和思瑞浦的產品同樣應用在5G基站。根據招股書顯示,2020年4月,華為哈勃以1.1億元受讓燦勤科技控股股東持有的1375萬股股份,每股價格8元。股權轉讓完成后,華為哈勃持有燦勤科技4.58%的股份,為后者的第四大股東。
燦勤科技也是華為的供應商之一,2019年,燦勤科技開始向華為供應產品,2017年-2020上半年,燦勤科技對華為及其控制企業的銷售金額分別為0.20億元、1.38億元、12.86億元、6.83億元,占營業收入的比例分別為16.76%、50.87%、91.34%、92.68%。
也就是說走到上市這一刻,燦勤科技九成收入來自華為。
但是有了華為的扶持,燦勤科技的業績也是直線上升,招股書顯示,報告期內燦勤科技實現營收1.2億元、2.71億元和14.08億元,增幅分別為126%、420%。凈利潤0.29億元、0.58億元、7.02億元,增幅分別為100%、1110%。
華為認購燦勤科技時,對應的估值為24億元,如今燦勤科技的市值為56.8億,實現了翻倍增長。華為哈勃認購價格為8元每股,如今截至發稿前燦勤科技的股價為14.2元,華為哈勃盈利超8000萬。
從燦勤科技和思瑞浦來看,華為哈勃在盡全力扶持一條成熟的產業鏈。隨著被投企業成功上市,未來發展也會增添一些確定性,被投企業的快速上市,也是在向市場表態,國產企業有能力突破卡脖子技術。圍繞芯片、5G、半導體的所有產業鏈,也都終將有條國產可替代的康莊大道。
突擊入股,最快一年半迎回報期
除了盡心盡力扶持被投企業之外,華為哈勃也有幾次“意在財務回報”的投資。
2020年11月東微半導體向科創板遞交招股書,招股書顯示東微半導體在提交申請前12月內新增了數名股東,其中便有華為哈勃的身影。

從股權變動的時間線來看,2019年12月,蘇州中和春生三號投資中心(有限合伙)將東微半導體1.57%股權、1.84%股權分別以1961.70萬元和2300.00萬元,轉讓給天蟬投資和智禹淼森。轉讓價格為28.25元。這次股權轉讓半年后,華為哈勃低價入股。
華為哈勃是在東微半導體遞交招股書前五個月突擊入股的。2020年7月,華為哈勃向東微半導體增資7530萬元,入股價格為22.61元。占股比例為7%。
此外,華為哈勃入股后半年,2020年12月,國策投資、智禹東微、豐輝投資、中新創投及上海燁旻,分別認購東微半導體新增股份2.26%、2.07%、0.94%、0.38%、0.19%,入股價格為52.54元。
也就是說,在東微半導體上市前一年的三次股權變動中,華為的入股價格最低。如今東微半導體的股價為234元,相較于華為哈勃22.61元的入股價格,翻了十倍。2023年2月東微半導體過解禁期,如果那時華為哈勃套現,可謂是一年半就迎來回報。
同樣在遞交招股書前五個月獲得華為哈勃突擊入股的,還有激光雷達傳感器廠商炬光科技。更能體現華為哈勃突擊入股的是,華為哈勃入股之時炬光科技已經處在IPO輔導階段。
根據炬光科技招股書顯示,2020年9月,華為哈勃以5,000萬元認購炬光科技增發的200萬股股份,其中200萬元計入注冊資本,其余計入資本公積。華為哈勃入股價格為每股25元,入股后持有2.96%股份。公開上市之后,華為哈勃持有炬光科技2.22%的股份。
截至發稿前,炬光科技的股價為154元,比華為哈勃入股的價格翻了六倍。
華為哈勃幾次的突擊入股,在外界看來都有純財務投資的感覺。但其實通過東微半導體和炬光科技的上市表現來看,華為哈勃的入股均給兩家做了背書,上市之后股價一路上漲。
如今在IPO階段的還有中科飛測、美芯晟、裕太微電子等。這家成立四年,還年輕的VC也要開始走上回報路了。
猜你喜歡
攜手華為 大有可為!萬興天幕2.0重磅亮相華為HDC2025
6月20日下午,全球領先的新生代數字創意賦能者萬興科技深化AI布局,攜萬興天幕音視頻多媒體大模型2.0及基于萬興天幕2.0能力底座打造的終端應用新品萬興天幕創作廣場亮相華為開發者大會2025(HDC 2025)。



 野馬財經
野馬財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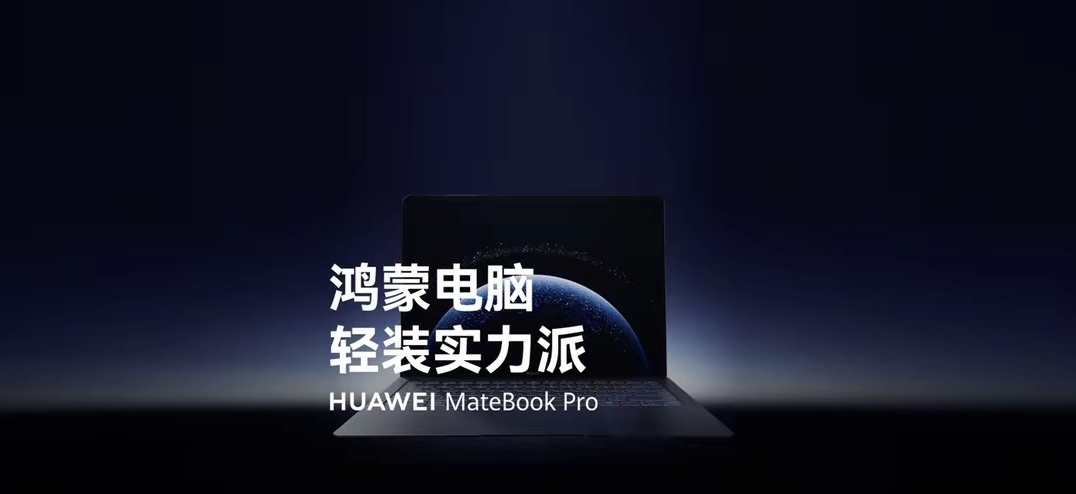
 博望財經
博望財經

 獵云網
獵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