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被制裁兩年后,國產EDA業能提供芯片設計所需十分之一工具
對華為來說,2019年5月17日注定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北京時間當天凌晨,華為突然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受到美國的第一輪打壓。第一輪的打壓手段主要是兩個:斷供美國芯片和軟件,斷供芯片設計必需的EDA(電子設計自動化)工具。
在中國“缺芯”之痛里,除了廣為人知的光刻機,EDA工具也是命門之一。這是一種對芯片進行自動設計的工具,特別是目前一顆芯片集成了幾億甚至幾十億的晶體管,肉眼難見,人工已經無法完成時,EDA自動化設計工具更是不可或缺。而目前國內85%的EDA市場份額被美國Synopsys、Cadence、Mentor三大巨頭壟斷。
自華為被制裁后,國產EDA工具進入戰時狀態。按照慣例,一個EDA工具簽訂購買合同,一般授權3年。事實上,被美國制裁后,華為內部也制定了一個EDA工具3年替代的方案。
如今兩年已經過去,我們獲悉,國產EDA在單點上取得突破,但還不能像美國巨頭那樣提供覆蓋全部設計流程的平臺。如果把國內所有企業的能力加起來,它們能覆蓋的芯片設計流程在10%以內。
華為和合作伙伴聯合攻關
一位芯片資深人士對我們說,2019年一家國內EDA龍頭企業已經實現盈利,有上市打算,突發華為被制裁事件后,華為天天找這家企業談,目標是兩三年之內要聯合解決EDA卡脖子問題。“一二三列出單子,這單子里邊哪些是你能做的,都劃下來做,其他你不能做的,華為自己做。”

圖 /視覺中國
“原來國產企業是沒有這樣的機會的。過去幾十年,芯片工業一直是全球化體系,大家習慣了用歐美現成的產品,國產工具做出來很少有人用。”上述資深人士稱,“現在有機會打破美國的壟斷,做世界級公司。所以這家國產EDA公司立刻決定把人馬擴充一倍。”當然,公司也因為擴張從盈利變虧損了,“但你不能不做”。
2020年,美國對華為做了第二和第三輪打壓,目標是斷供華為高端芯片制造,導致華為手機麒麟芯片、電腦和服務器鯤鵬芯片都無法進行生產,華為芯片設計部門海思遭遇重創。在今年的一次大會上,華為輪值副董事長徐直軍稱,華為會繼續養著海思團隊。但華為芯片業務的暫緩,對于EDA的進程或多或少會有影響。
另一方面,從2020年底開始,華為旗下投資公司哈勃科技開始投資EDA工具。
僅僅在3個月內,華為哈勃就投資了湖北九同方微電子、無錫飛譜電子和上海立芯軟件三家國產EDA企業。AI財經社了解到,這些企業基本都處于早期。
其中,湖北九同方是成立時間最長的,董事長萬波曾任Cadence公司高級工程經理。一位行業人士了解到,過去三年九同方的業務主要是面向當地研究所,給某些項目提供設計服務,年銷售額大概幾十萬元,產品化尚處于早期。上海立芯則是一家2020年剛成立的公司,根據公開資料,公司董事長陳建利是學院派出身,還沒有商場實戰經歷。
芯片設計流程極為復雜,前后大體包括了前端設計和仿真、后端設計及驗證、signoff檢查、數據交付代工廠等階段。無錫飛譜對華為的整機產品有幫助,更多偏后端。
業內分析,華為把這些還只有初步技術的初創企業作為“備胎”,先解決以前這些企業產品沒人用的問題。
目前國內一線的EDA企業主要有華大九天、國微集團、芯和半導體、芯華章、概倫電子等公司。
據AI財經社了解,華為本來想投資像華大九天這樣的一線企業,但這些公司已經拿到了很多融資,規模都是億元起步,有的更走在了即將IPO的路上。目前華為和這些企業主要是圍繞某些項目進行業務合作。
填補15年空白之殤
除了華為,芯片熱讓資本相繼涌入EDA行業。2020年,概倫電子完成數億元人民幣的A輪融資;國微集團旗下的思爾芯完成數億元融資。2020年成立的初創公司芯華章更是一年內拿了四輪融資。
此外,一些成立10年以上的國產EDA企業有望在今年登陸資本市場。目前華大九天、國微思爾芯、概倫電子、廣立微4家企業都已啟動IP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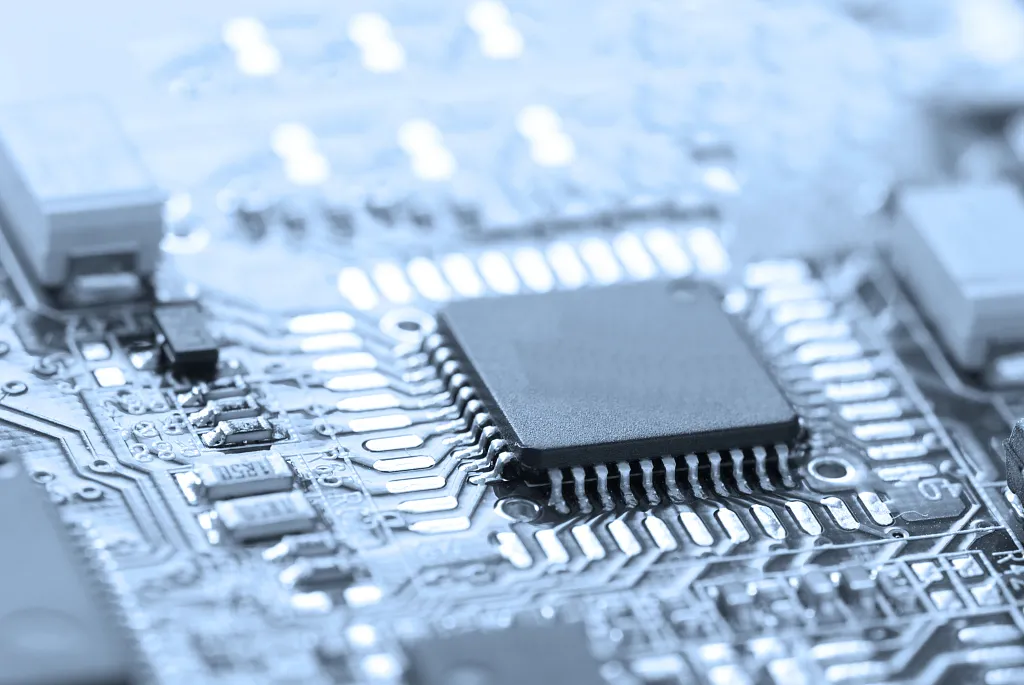
圖 /視覺中國
但整體來看,幾家EDA公司更多在于點狀突破,比如華大九天在前仿真,芯和專攻后仿真,廣立微在良率測試,國產EDA公司還不能提供像國際三大巨頭那樣對芯片設計全流程進行覆蓋,提供平臺化服務。
因此這些企業營收規模也不大。據AI財經社了解,目前除了華大九天每年能有4億-5億元營收,其他一線公司營收普遍在1億元左右,估值也較低,因此還不是國家大基金的扶持重點。
“如果給公司10倍估值,大基金入股20%,可能在兩個億,這對于大基金上千億的盤子來說很小,他們手里有幾百個項目,管不過來。”一位EDA行業人士稱。目前只有體量最大的華大九天得到了國家大基金的扶持。天眼查APP顯示,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持有華大九天14%的股份。
這種羸弱的現狀和行業過去15年的空白息息相關。國產EDA的發展之路曾上演了計劃體制下國家主導的自主萌芽、市場打開后外部沖擊的混亂年代、民企創業和崛起,和如今的國產化為目標的戰時階段。
1988年,在“巴統”協議對中國高科技禁運的背景下,國外EDA工具無法進入國內,我國曾動員了全國200多名專家聚集北京集成電路設計中心,開發出了國產EDA工具“熊貓系統”。但在1994年禁運取消后,“造不如買”的大潮讓美國企業快速占領了國內EDA市場,國產EDA企業無人問津。
直到2009年,繼承了“熊貓系統”的華大九天正式成立,在隨后幾年里承擔了“十一五”、“十二五”國家核高基EDA重大專項,同時,芯和、博達微等一批國產EDA企業成立,整個行業才重新起航。
而自華為事件之后,國內EDA企業數量大增。根據芯思想研究院的統計,2020年中國EDA公司保有數量28家,而在2017年只有16家,3年時間EDA公司保有數量增長了75%。
但在過去,“沒有客戶愿意用”是中國芯片行業的普遍困境,處在產業最前端的EDA工具更是如此。
一位行業人士總結,最初美國三大巨頭也像國內企業這樣,只有單點能力,但它們靠著多起并購不斷壯大,發展了三四十年,每年投入巨額的研發費用,目前已經形成了成熟的全平臺能力。
“國內高科技的產品迭代都非常快,比如手機6個月就要出新品,使用國外公司的全流程對于國內芯片設計公司是最高效的,出于商業考量,國內芯片企業并沒有動力來和國內EDA企業做適配。”
環境在悄悄發生改變
但自華為事件發生后,不少國產EDA企業開始享受到紅利。
一家國產EDA企業透露,今年有越來越多的國內用戶開始切換到國產EDA上來。一類是像華為這樣受到美國打壓的公司,另一類是一些即將IPO的企業,此前有些企業并沒有購買正版的EDA軟件,但是上市意味著所有的業務必須正規化,而國外EDA工具太貴,因此這些公司也在尋找可替代的軟件方案。
另一部分商機源自過去兩年國內成立的2000多家新興的芯片設計企業。這些小公司有些沒有標準的設計流程,因此沒有歷史包袱,不一定非要用誰家的平臺,而且芯片產品也沒有那么復雜。一般國際三巨頭的產品都是平臺售賣,不會拆出某個工具單賣,全套價格高達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小企業無法承擔,而國內企業單個工具價格在十幾萬或者幾十萬元之間,相比起來更加便宜。
國產EDA的生存環境發生了改變。一方面因芯片賽道受重視而獲得資本青睞,另一方面受益于市場的需求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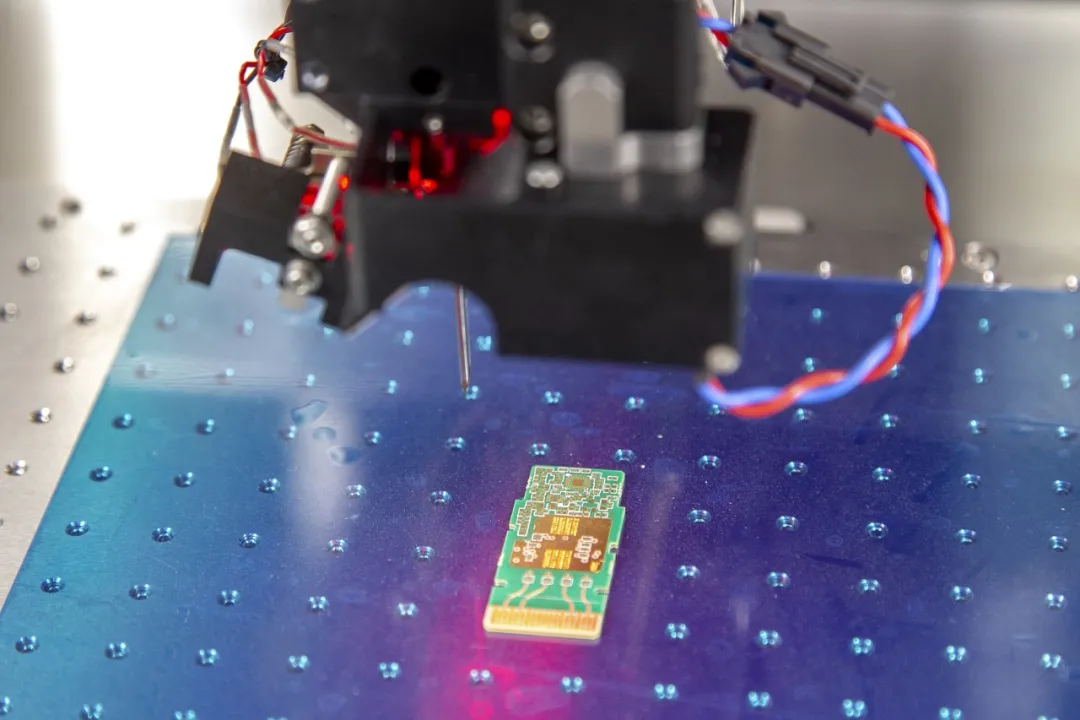
圖 /視覺中國
當然,伴隨著機遇,行業也有一些浮躁的現象出現。比如折戟在芯片上市潮中的國產EDA第一股“芯愿景”。被客戶舉報拖欠557萬元發票是一大導火索,另一大主要原因是,芯愿景的核心技術頗受爭議。
一位業內人士對AI財經社說,芯愿景主要提供反向工程服務,就是把一些公司的芯片拆解,還原里面的電路圖、器件布局,再把設計圖賣給其他廠商,“這類灰色地帶的生意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如果這樣的企業能上市,對整個EDA行業的聲譽其實是一種傷害。”
在多位EDA人士看來,目前國產EDA行業只有沉下心來,做好單點突破,做出一些特色化的產品,才有望在之后串聯起更多的應用和流程,這也是唯一的路。
而觀察美國幾家芯片巨頭,EDA的壟斷還體現在與生產廠如臺積電等的捆綁上,因為沒有這些與制造廠的捆綁,芯片設計公司其實是沒辦法用到EDA工具的。美國三大巨頭在構建生態上無一不把芯片制造廠作為重中之重。現在國內的幾家領先EDA公司,也都是在生產線的生態圈構建上花了很多力氣。“可以說找到了問題的關鍵。”無論是華大九天還是芯和,在全球和國內的晶圓廠先進工藝上都取得了認證。
總體來說,現在還處于單點突破的國產EDA企業,在芯片國產化道路上仍道阻且長。
猜你喜歡
攜手華為 大有可為!萬興天幕2.0重磅亮相華為HDC2025
6月20日下午,全球領先的新生代數字創意賦能者萬興科技深化AI布局,攜萬興天幕音視頻多媒體大模型2.0及基于萬興天幕2.0能力底座打造的終端應用新品萬興天幕創作廣場亮相華為開發者大會2025(HDC 2025)。



 野馬財經
野馬財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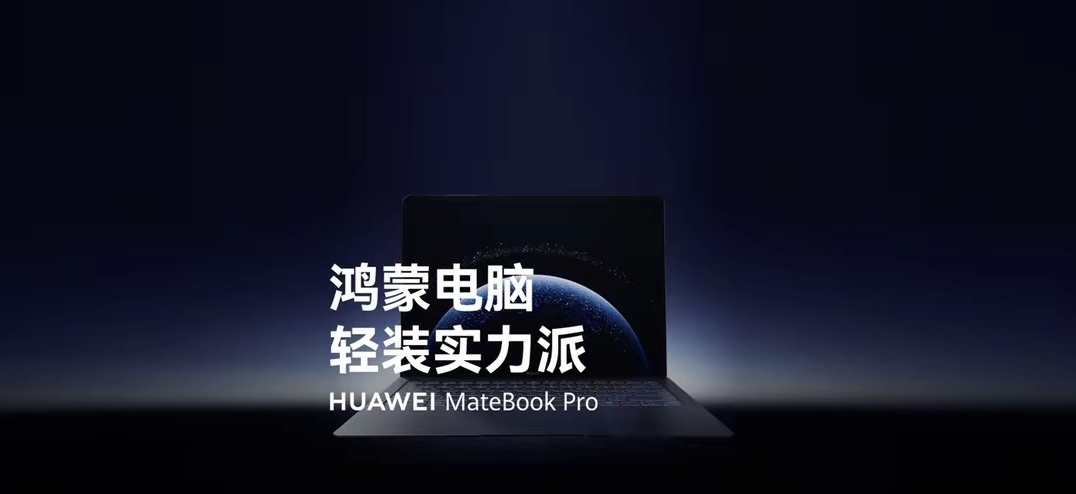
 博望財經
博望財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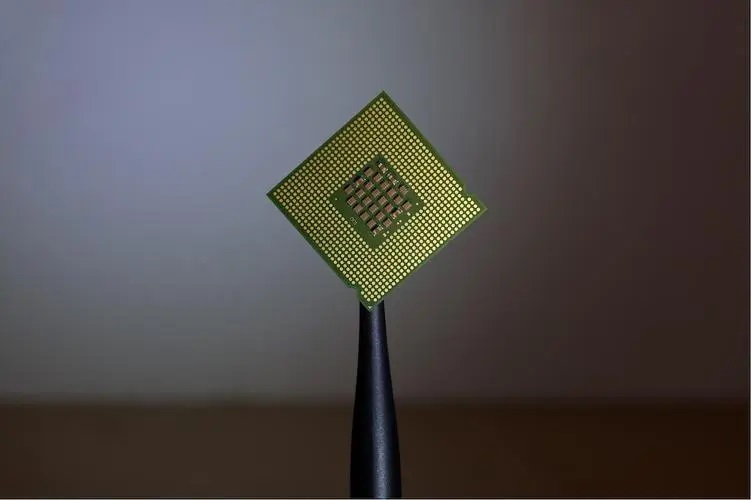
 獵云網
獵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