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說李錄比段永平更厲害,我佛了
你可能不常看見李錄的名字。但凡看到,大概都在說“很厲害”。
此人有多厲害?先給幾個坐標。
他站在傳奇投資家的肩膀上,芒格、巴菲特都對李錄投入了金錢的背書。巴菲特經由李錄推薦買了比亞迪,大賺了幾十倍;芒格則說自己活了95歲,這輩子把家族財產交給外人管理僅有李錄一例,那話說得好,“比李錄更出色的人寥寥無幾”。
李錄的知識也令人嘆為觀止。他是位學者式人物,身懷著百科全書式的學問和洞見,諸位聽過讀過他采訪和課程記錄的應該有印象,講起話來一片真誠。一位媒體前輩還告訴我,他認為,李錄比某幾位做學問的學者“看中國看得通透多了”。
甚至我看到有人寫文章,說“李錄比段永平厲害”。人家段永平什么人?國內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轉行投資,出手就“不輸巴菲特”。被認為比如此頂尖的投資人更厲害,是要有多出奇的本領?
當然啦,話說回來,拿投資人和投資人比高下,顯得挺無禮的。但“比較”本身是有價值的,至少可以弄明白,李錄和其他人的思維差異是啥,做了哪些不同的取舍,得到了哪些不同的結果和結論。
也才更能回答那個問題:為什么李錄說很厲害?
1
特別“特別”
要談投資人,先談事業。
李錄執掌的喜馬拉雅資本,特別特別。
官網的信息量就已經很大了。公司創辦于1997年,秉承巴菲特、芒格的價值投資,專注亞洲和美國的長期投資機會,近年主要關注亞洲(尤其是中國)上市公司,AUM超過100億美元。雅虎財經有個說法:“據多方信源,自1997年成立以來,喜馬拉雅資本的年回報均保持在超過20%的水平”。
這個“20”,是個大寫的“穩”字。
要知道,喜馬拉雅資本的這二十幾年,穿越了1997年的金融危機、2001年的互聯網泡沫、2008年的金融危機還有2015年的股災,每隔幾年就趕上“百年不遇”的危機,二級投資涼了一批又一批。
危機背后的“穩”,一定藏著個“狠”。
近看喜馬拉雅資本,又是個大寫的“藝高人膽大”。
它身上有一些巴芒企業的影子。與伯克希爾哈撒韋類似,喜馬拉雅資本團隊精簡。李錄曾在訪談提及,伯克希爾市值5000至6000億美元時,總部人員(包括巴芒)也不過20人。LinkedIn顯示,喜馬拉雅資本,這家百億美元aum的投資機構,團隊規模還不到10人。
更大膽的來了。李錄的基金采取與“沃倫”、“查理”早期合伙人基金一樣的管理費制度,把自己直接放到一個類似劣后級的位置——不收管理費,復利年收益的前6%全歸LP,超過6%的部分提取25%。
這就是與巴菲特、芒格共事最高級別的bonus——見過他人意想不到的可能性。我敢打賭,如果在北京做人民幣基金,大部分人可能連“不收管理費”這層問題都不會考量。
不收管理費這事,放到中國乃至全球都極為罕見。
通常來說,GP管理費率在2%上下,產生超額收益再拿分成。按正統的投資價值觀,能力強的GP追求的肯定是Carry,但放眼最頭部的基金們,也沒見誰自信得連管理費都不要了啊!
管理費之于GP,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現金流,甚至是“兜底”。喜馬拉雅資本百億美元aum,管理費按2%算,一年至少10億人民幣以上現金。那么,不收管理費,又意味著什么?
首先意味著不缺錢,二來是充分的回報自信。喜馬拉雅資本團隊夠小,回報夠好,沒有龐大的資金壓力。李錄對投資的追求也很高,即使論下限,也超過了多數投資人,“保底”從來不在考慮范疇。
更深一層,不收管理費,也是對投資自由的追求。
價值投資的理念,要投看得懂且剛好價格便宜的東西。在這樣的框架下,李錄對項目的“待機時間”極其驚人。他曾提到兩個案子,一個花5年研究透,再花2年等價格,入手之后居然又持有7年,另一個持了長達22年,中間經歷過兩、三次腰斬式暴跌,李錄也“沒想過放棄”。
若換作其他機構,這事幾乎不可想象。且不說上哪找這么長周期的錢,光看這如此稀薄的營業頻率,哪里經得起LP以年度為單位的業績拷問?
不收管理費,不在最開始就必須值這個錢,恰恰可以解決問題。用李錄的話說,“不會因為短期利益患得患失,或是激進或是怯懦”。犧牲短期利益,換取長期的投資自由,讓每次出手多幾分無壓力的質感,這大概也是李錄的長期主義。
2
職業的原則
《底片》曾經寫過兩位出手頗具魄力的投資人。
一位是段永平,入手網易股票的架勢是,“做足功課后,基本上把能動用的錢全部用了”。另一位是做早期投資的“狙擊手”劉芹,不撒胡椒面,首期美元基金1.5億的近半數都拿來押小米,早期項目快手直接放了2億多美元。當然,他們也因此賺到了一般人賺不到的大錢。
相比之下,李錄的出手更加大手筆,也更加集中。
2020年11月,美國SEC披露了2020年Q3喜馬拉雅資本的美股組合,13.1億美元的規模只持有4支股票:美光科技(Micron)、Facebook、美國銀行和谷歌。其中,第一重倉美光科技占了足足41.9%倉位,持股市值5.4億美元。
這還沒完。2020年12月下旬,李錄及喜馬拉雅資本增持郵儲銀行H股,累計持股10.06億股,持股占比5.06%。按照當時股價計算,這筆持倉價值超過40億港元。一個月之后,郵儲銀行股價大漲超過20%。
這重倉的魄力,當真是個狠人。
或許有人認為,大手筆是因為彈藥多,現在誰不把重倉掛嘴邊?畢竟好標的可遇不可求,錢多的GP可多了去了。放李錄這,恐怕還真不是這么回事。
李錄曾經表示,基金對新投資人一般是關閉的,除非機會比手頭資金更多。這話大概率不是凡爾賽,畢竟頭頂“中國巴菲特”的官方蓋章,要做個超大基金盤子,想必也不是問題。
說到這,有必要聽聽李錄對自己的評價:“不追求資產管理規模,只希望留下一份干凈的投資記錄”,“用最干凈的方法,僅憑智慧賺應得之錢”——說通俗點,不求做大做強,就是想站著掙錢。
我猜,這大概就是李錄主觀上的價值投資的表現了,和其他投資不是同一種職業。這種職業的特殊性,就是可以“以我為主”,而把客觀能力保持在一個恰當的口徑里。
這可以從巴菲特那則關于棒球的故事說起。李錄說這套方法對其影響很大,他是這么轉述的:
“泰德?威廉姆斯把擊打區劃分為七十七個棒球那么大的格子。只有當球落在他的‘最佳’格子時,他才會揮棒,即使他有可能因此而三振出局,因為揮棒去打那些‘最差’格子會大大降低他的成功率。
作為一個證券投資者,你可以一直觀察各種企業的證券價格,把它們當成一些格子。在大多數時候,你什么也不用做,只要看著就好了。每隔一段時間,你將會發現一個速度很慢、線路又直,而且正好落在你最愛的格子中間的‘好球’。那么你就全力出擊。如此,不管你的天分如何,你都能極大地提高你的上壘率。”
這里,李錄把他對客觀判斷的部分描述為“七十七個棒球格子”,做出決策的標準,就簡化為尋找你所熟知的那幾個格子,全力出擊。在此之外,不做任何動作。
這套方法聽起來簡單,但其實內含兩個非常困難的問題:第一,構建“七十七個棒球格子”,第二,自律。
自律,一件多么困難的事情!現代人愛講“自律給我自由”,但反過來說,自律更是需要自由為提前。你要想辦法“往里走,安頓自己”,就得有充分的自由的時間花在自己身上。
沒有自由,就沒有自律的權利。
所以李錄在解決第二個難題之前,先解決的是“自由”的問題,這里就跟我們之前討論過的段永平、龔虹嘉這些人有點像了。
3
比段永平如何?
價值投資如今成一門顯學了,人人頂個帽子,得精髓的卻沒幾個。
找巴菲特吃過飯的段永平算一個。200萬美元投資網易賺了1個億,“不輸巴菲特”的投資水準,讓他早早被冠上“段菲特”的名號。價值投資信奉“買股票就是買公司”,但段永平曾經放話,真正理解并相信這句話的人,在他認識的人里不超5個(包括巴菲特和芒格)。
李錄肯定也算一個。要知道,李錄是芒格親口蓋章“中國的巴菲特”,也是芒格家族基金的唯一管理者,倆人吃了十幾年午餐。
中國人有個習慣,好比較,凡事必須分出個勝負。比如就有人認為,李錄比段永平更強。
這二位的投資成績似乎都不輸巴菲特,但咱畢竟也沒法把倆人的IRR拿出來做比較。非要比比看,那就不比強弱,只比差異。
《底片》曾經寫道,極致的自由是段永平的投資絕招——不做職業投資人,沒有基金框架的束縛,不會頻繁現身,但凡出手就是絕招制勝。但究其動機,其實簡單得很,“不希望把這個作為一個職業,職業意味著很多責任”。
段永平是個對身份沒有訴求、欲念的人,把投資作為職業,對于功成名就的企業家段永平而言,既無意愿,也沒必要。
李錄就太不一樣,他是這份職業的“天選之子”。
絕頂聰明,天然好奇,遇到貴人,三個如此稀缺的特質,李錄湊得齊齊整整。李錄是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學士、商管學碩士和法學博士,三個學位僅用了6年。25歲時聽到巴菲特演講,誤打誤撞進入投資領域,30幾歲遇到芒格,擁有了終身的投資伙伴和人生導師。從業二十幾年,依然有著相當高的投資興趣和效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他不排斥職業責任,也不像一些投資人感覺“痛苦”。他創辦喜馬拉雅資本,還幫芒格家族管錢。更難得的是,即便在基金的框架之下,依然通過制度設置實現了投資自由,這種自由的質感是更加難得罕見的。
再看看二人的打法,風格都很鮮明。
段永平是個頂級商業人才,天生擁有摸得準商業命脈的money sense。翻看段的投資語錄,通篇行業、業務和數字,話里話外圍繞的都是生意。
如果說段永平的投資基礎是經驗和sense,李錄就是知識。而且,李錄最成功的案子,居然源于不相干的知識。
“最成功的幾個案例里面,知識的來源其實還真的不是年報,而是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識,讓我對一些其他的問題做出比較不同于市場的判斷,有一些真正的、獨特的洞見”。
翻看李錄的分享,總覺得不像個投資人,更像個學者或者經濟學家。一位媒體前輩告訴我,李錄看中國,比XXX、XXX、XXX這一波人看得通透多了。李錄新書《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公開了一組書單,除了投資,還涵蓋了科學、哲學、歷史、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投資這件事,也常被他放在非常宏觀的視角當中——回答投資問題時,他慣于從更高一層維度來闡釋。
張磊曾在《價值》一書中提到,最好的方式方法未必是使用估值理論、資產定價模型、投資組合策略,而是堅持第一性原理,即追本溯源,這個“源”包括基本的公理、處世的哲學、人類的本性、萬物的規律。
李錄顯然身懷這種融會貫通的百科全書式本領。這種本事,也是他高于“生意人”的一個特質。
但更接近本質的東西,還是人生觀。
段永平做人做事的理念叫做本分,極度清楚自身的能力邊界,運用可行的模式,在恰當的時點后發制人,一遍一遍、穩穩當當把錢賺到,功成名就之后,退居二線深居簡出。
李錄呢?更接近一種“苦行僧”的狀態。
他對人性的弱點十分敏感和警醒,認為市場的存在就是專門發現和考驗人性的弱點。他崇尚巴芒二人的淡泊名利,強調對知識保持完全誠實。他追求智力、修養、精神上持續的自我超越,在他的眼中,價值投資已經不僅是思維方式和預測方法,也是一種行為準則。
李錄不光對外部世界下功夫,還花了很大的能量處理自己。
三省吾身,這是種職業素養,也可以認為是種人生觀。巧的是,這是最適合投資這份職業的人生觀。當然,這么講有點幸存者偏差,但站在李錄的角度去推論,就知道他在舍棄什么,選擇什么,而這些取舍也是李錄和其他投資人最根本性的差別。
大部分以投資為職業的人,要把時間花在外部世界,不信你問問,投資人在咖啡館里的時間永遠比在辦公室多。假如你做一級市場,你得花費大量精力去識別他人的能力、缺陷,去研究他人創造的商業模式,付出更高的時間沉沒成本,甚至要和競爭對手陷入纏斗;假設你做資管,求規模,你就要不停地去應付LP,不間斷地出手,擴大團隊,做管理。
李錄愛說投資人的世界是一個熵減的世界。你想,外部世界的增減是無法控制的,要做到熵減,他也只能“往里走”。
回來再琢磨一下李錄的職業追求,“不追求資產管理規模,只希望留下一份干凈的投資記錄”,“用最干凈的方法,僅憑智慧賺應得之錢”。投資之于李錄,表象是一份職業,實際上,則是主觀世界的自我實現和價值追求。
李錄、段永平二人的最大區別,大抵在這了。兩人都是頂尖的商業人才、價值投資人,只不過,段永平是“商魂商才”,而李錄更接近“士魂商才”。
4
“人劍合一”
這樣的對比,也不是全然是無聊,或者博人眼球——某種程度上,這解釋了芒格對李錄異乎尋常的青睞。
已經活成傳奇的芒格,對李錄的評價有多高?
2008年,84歲的芒格在采訪中提到,“人的一生不需要做很多投資,我的財富主要來源于三次投資:一是伯克希爾,二是好事多,三是李錄的喜馬拉雅基金”。
2019年,95歲芒格在股東大會再次表示,“李錄不是常人,他是中國的巴菲特”。芒格說,李錄在尚未過度捕撈的中國市場“捕魚”,而且那里還有魚,95年間,芒格家族的財產交給外人管理僅此一例,找到了李錄不會再找別人,也不知道去哪再找一個李錄。
這可是投資傳奇人物芒格的公開評價。李錄憑什么?
憑能力和聰明嗎?巴芒二人身邊,不可能沒有比李錄還要聰明能力強的人,翻翻這些年網傳的一眾伯克希爾接班人簡歷,一下就清楚。
憑李錄既懂美國市場也懂中國市場嗎?這樣的人也絕不在少數。要知道,海歸早就是投資人才的標配設置了。
憑李錄拉著巴芒二人投資比亞迪賺了超高回報嗎?這件事上,更多證明的是巴芒二人對李錄真金白銀的信任和背書吧,而不只是李錄的投資眼光有多狠。
那李錄他到底憑什么?
通常來說,前輩對后輩真情實感的欣賞和背書,肯定不止于聰明才干、經歷背景這類過于顯性的東西。這個事,必須且只能從內里來看。
通過與段永平的對比不難發現,李錄是個離標準意義投資人很遠,卻離巴芒二人核心理念最近,行為模式上也最相像的職業投資人,他的職業理想乃至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幾乎完全匹配了價值投資的職業要求,幾近“人劍合一”了。
《底片》欄目介紹:拆解最有價值的案例,記錄最值得關注的人物,用“分析+素描”的寫作方式,同時向GP、LP和讀者提供閱讀價值。換一種語境,透視投資價值。
猜你喜歡
蘇州銀行:金融科技點亮新質生產力,創新引擎驅動服務升級
蘇州銀行秉持“以客戶為中心”的一體化經營戰略,致力于通過金融科技的力量,為客戶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務。



 獵云網
獵云網
 投中網
投中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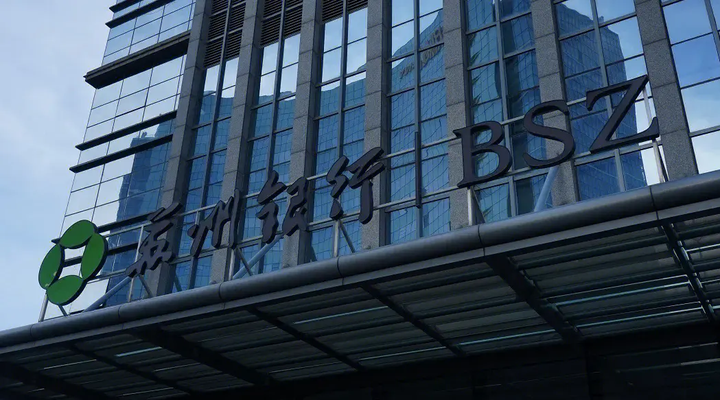
 博望財經
博望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