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APP脫單靠譜嗎?有95后在第九次見面找到真愛,也有人掉入“殺豬盤”
輸入“殺豬盤”,點(diǎn)擊回車,搜索引擎出來2800萬條結(jié)果。這2800萬條內(nèi)容中,有一類是案例報(bào)道,河北、廣東、江蘇、浙江……幾乎各個(gè)省份各個(gè)地區(qū)都有想要尋找愛情卻又被騙走幾十萬錢財(cái)?shù)娜恕?
你還敢相信網(wǎng)戀嗎?很多70后、80后會(huì)覺得社交平臺(tái)上充滿了陷阱,到處是騙錢、騙色、騙感情的“殺豬盤”,但同時(shí),又有數(shù)據(jù)報(bào)告顯示,44.6%的95后通過社交軟件成功脫單,受訪單身人士中,有32.5%的人認(rèn)為圈子太小,交際圈太窄。

平臺(tái)“脫單”新思路
“我媽每打三個(gè)電話,至少有一個(gè)是催我找對(duì)象的。”在北京工作的小易經(jīng)常被催婚,盡管她才26歲。為了避免再次被同樣的事情煩擾,她決定主動(dòng)出擊,“不行了,必須要解決這個(gè)問題。”
小易的解決方案非常年輕人,直奔社交平臺(tái)。網(wǎng)絡(luò)交友的負(fù)面新聞她并不是不知道,但小易認(rèn)為,相比熟人介紹,大城市的年輕人通過社交平臺(tái)脫單更靠譜,“遇到正確的人,這個(gè)概率是一定的,如果樣本足夠大,就會(huì)早一點(diǎn)實(shí)現(xiàn)。”
小易最先想到的是世紀(jì)佳緣、珍愛網(wǎng)之類的傳統(tǒng)婚戀網(wǎng)站,甚至考慮過充會(huì)員。一個(gè)從業(yè)者的帖子讓她及時(shí)轉(zhuǎn)換了方向。“他提醒,早期的相親網(wǎng)站已經(jīng)過了紅利期,上面的內(nèi)容參差不齊。現(xiàn)在是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很多基于小程序的相親交友平臺(tái)正在拉新階段,對(duì)于用戶的質(zhì)量要求比較高,審核也更嚴(yán)格。”這名專業(yè)人士的視角,讓小易有了新發(fā)現(xiàn),一批以前沒有聽說過的新社交平臺(tái)進(jìn)入她的視線。
而程序員楊澤注冊(cè)T平臺(tái)的時(shí)候,想的非常清楚,“我談戀愛特別費(fèi)勁,因?yàn)楹π摺N也恢栏思伊氖裁矗膊恢涝撛趺慈チ奶欤沂钦f嗨?還是說很高興認(rèn)識(shí)你?還是發(fā)一張表情包什么的?”
整天只有工作的楊澤想“找個(gè)地兒練一下,希望有一個(gè)能跟真實(shí)的女孩交往、鍛煉的機(jī)會(huì)”。這其實(shí)是大多數(shù)年輕人的困境,周圍有限的熟人,要么是同學(xué),要么是同事,即使想要脫單,也有心無力。
一旦有了強(qiáng)烈的動(dòng)機(jī),挑選并注冊(cè)社交平臺(tái)就會(huì)迅速推進(jìn)。小易選擇的是P平臺(tái),原因非常簡單——安全。“他們強(qiáng)調(diào)面對(duì)面交流仍然是人們相識(shí)相知最有效的方法。在平臺(tái)上不能聊天,只能線下見面。而按照規(guī)則,只有雙方互相打招呼,才能約線下見面,見面地點(diǎn)也由平臺(tái)指定,通常是連鎖咖啡店。”
這正好符合小易的認(rèn)知,她認(rèn)為見面聊天效率是最高的,“如果是騙子,應(yīng)該也不會(huì)選擇直接跟人見面這種方式吧?”
其實(shí)不管是網(wǎng)頁時(shí)代,還是小程序時(shí)代,安全依然是陌生人社交的第一訴求。早期的校內(nèi)網(wǎng)曾經(jīng)聚集了最大規(guī)模的實(shí)名制大學(xué)生,34歲的大藍(lán),算是比較早“網(wǎng)戀”的一批人。2006年時(shí),大藍(lán)在校內(nèi)網(wǎng)無意中加了一個(gè)男生,初衷很簡單,男生的頭像是古天樂,那是大藍(lán)的偶像。這個(gè)無意,其實(shí)背后有算法的支撐,“古天樂”是大藍(lán)一個(gè)大學(xué)好友的高中同學(xué),在瀏覽好友頁面時(shí),旁邊會(huì)有關(guān)聯(lián)人物推薦。
“那會(huì)兒校內(nèi)網(wǎng)的推廣海報(bào)瘋狂貼滿校園大大小小角落,當(dāng)時(shí)我還年輕,對(duì)未知的人和事都有一種近乎夸張的熱情和好奇,得空就在上面不停點(diǎn)擊,請(qǐng)求加好友。”大藍(lán)對(duì)于加好友的風(fēng)險(xiǎn)并非沒有評(píng)估過,但她認(rèn)為,根據(jù)學(xué)校、院系信息基本可以定位到一個(gè)準(zhǔn)確的人,還能看到這個(gè)人的關(guān)聯(lián)同學(xué),信息相當(dāng)真實(shí)。
一個(gè)月瘋狂約九個(gè)網(wǎng)友,最后一個(gè)成為男友
1967年,美國哈佛大學(xué)心理學(xué)教授斯坦利·米爾格蘭姆通過實(shí)驗(yàn),提出了一個(gè)有意思的假說——“六度分割”,即最多通過6個(gè)人你就能夠認(rèn)識(shí)地球上任何一個(gè)陌生人。

但是在陌生人社交時(shí)代,沒有明確的指向性,你可以很輕松認(rèn)識(shí)一個(gè)陌生人,也可能永遠(yuǎn)找不到那個(gè)對(duì)的人。但你看到的每一個(gè)人、認(rèn)識(shí)的每一個(gè)人,都離不開算法的推動(dòng)。
楊澤在T平臺(tái)上,依靠對(duì)方填寫的信息來判斷是否合拍,他認(rèn)識(shí)的第一個(gè)女生,兩者擁有共同的興趣是戲劇。這也是社交平臺(tái)的主流思路,鼓勵(lì)用戶填寫個(gè)人標(biāo)簽和興趣愛好等資料,根據(jù)標(biāo)簽來提高互相匹配的概率。
但是接觸之后,楊澤發(fā)現(xiàn)雙方生活秩序并不同步。半年之后,在會(huì)員到期的前一天,楊澤發(fā)現(xiàn)一個(gè)女生為自己點(diǎn)了“超級(jí)喜歡”。這是一個(gè)產(chǎn)品經(jīng)理,看似和他毫無交集,但點(diǎn)進(jìn)去發(fā)現(xiàn)“是一個(gè)比較誠懇的女生”。在之后的聊天中,楊澤越來越發(fā)現(xiàn),“她給我的感覺特別不一樣。”
這讓他既興奮又困惑,“找對(duì)象這個(gè)事,你讓我自己選,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我喜歡什么樣的人。但是算法直接給我推薦的,都是我喜歡的。感覺我被算法給吃透了,真想知道它是怎么推送的?”
其實(shí),社交平臺(tái)的招數(shù)都差不多,盡可能精確地定義每一個(gè)用戶,然后讓用戶盡可能多的交流。比如,對(duì)個(gè)人填寫的資料進(jìn)行匹配,創(chuàng)建年輕人感興趣的話題來打通彼此之間的交流通道,或者用一些好玩的黑科技增加趣味,做一些夫妻相之類的小游戲。
小易在P平臺(tái)上,除了填寫興趣愛好價(jià)值觀等內(nèi)容外,系統(tǒng)還疊加了位置因素,這很契合她的理念,短距離交往,效率更高。“北京太大了,我在平臺(tái)上約見面的其中一個(gè)男生,見了三次,花了一個(gè)月時(shí)間。后來成為她男友的平臺(tái)網(wǎng)友則不同,因?yàn)閮扇俗√幹桓粢粭l馬路,一周可以見三次。”
在小易的認(rèn)知中,在陌生人社交模式下,只有經(jīng)常見面了解,才能建立信任,推動(dòng)關(guān)系發(fā)展。而北京這樣的城市,每天通勤時(shí)間普遍要超過兩個(gè)小時(shí),如果離得太遠(yuǎn),再跨越半個(gè)城市來見面,交往成本太高。“6月9日到6月27日之間因?yàn)楸本┮咔榉磸?fù),沒有約見面,不算疫情的話,基本一個(gè)月見了9個(gè)人,第9個(gè)確定成為男朋友。”
“沒有抱著一定要成功的心態(tài),就是試試而已。”這樣密集的約見,對(duì)于小易來說還有另外一重意義,“這個(gè)過程,其實(shí)是在不斷調(diào)整自我認(rèn)知,對(duì)自己更了解,對(duì)自己的需求更了解。”
楊澤在與第二個(gè)女生交往的過程中,意識(shí)到一件事情,自己原本的害羞性格,其實(shí)是不相信會(huì)被人喜歡,“以前上學(xué)的時(shí)候,我覺得女孩喜歡的男孩應(yīng)該是體育委員或者學(xué)霸那樣的,但我都不是。工作以后,女孩可能喜歡同事中表現(xiàn)最好的、或者比較風(fēng)趣的,我覺得我也不是。”
T平臺(tái)帶給他一個(gè)新奇的發(fā)現(xiàn),原來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即使你普普通通,就真的有特別喜歡你的人。“一開始甚至很難想象是怎樣一個(gè)劇本,我竟然能從一個(gè)社交軟件認(rèn)識(shí)一個(gè)女孩,而且兩人發(fā)展成相當(dāng)親密的關(guān)系。”
一個(gè)月就脫單的小易認(rèn)為自己很幸運(yùn),但這種幸運(yùn)有方法論支撐,甚至可以復(fù)制,“相比熟人介紹,社交平臺(tái)更適合大城市的單身人士。但是前提是,搞清楚為什么要脫單,確定目標(biāo)后要投入時(shí)間,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wǎng)。”
但是她也強(qiáng)調(diào),“社交平臺(tái)只提供兩個(gè)陌生人認(rèn)識(shí),你要保持警惕,當(dāng)然也不要受太多網(wǎng)上交友負(fù)面新聞的影響,畢竟重要的是兩個(gè)人之后的相處,真正的磨合在戀愛之后。”
(應(yīng)受訪者要求,楊澤、小易、大藍(lán)均為化名)
猜你喜歡
蔣凡重啟阿里:一場AI重構(gòu)內(nèi)核的千億實(shí)驗(yàn)
蔣凡對(duì)阿里的重新定義,是一場組織、戰(zhàn)略與技術(shù)的三位一體變革。摯文集團(tuán)五年連跌,困局何解?
只要錯(cuò)過一個(gè)風(fēng)口、忽視一次用戶需求變遷,那么它錯(cuò)過的將是一個(gè)時(shí)代。知乎:2024Q1營收9.61億,職業(yè)教育同比增長35.9%
毛利率從去年同期的51.5%提升至56.6%。抖音電商女性消費(fèi)增長65%,“她經(jīng)濟(jì)”成就美好生活
全域興趣電商為女性創(chuàng)業(yè)和事業(yè)發(fā)展提供了趣緣連結(jié)、品類細(xì)分、供需匹配等多方面的支持。騰訊NOW直播將于12月26日關(guān)停
即日起,NOW直播將停止新用戶注冊(cè)及充值服務(wù),NOW直播網(wǎng)頁端產(chǎn)品服務(wù)停止運(yùn)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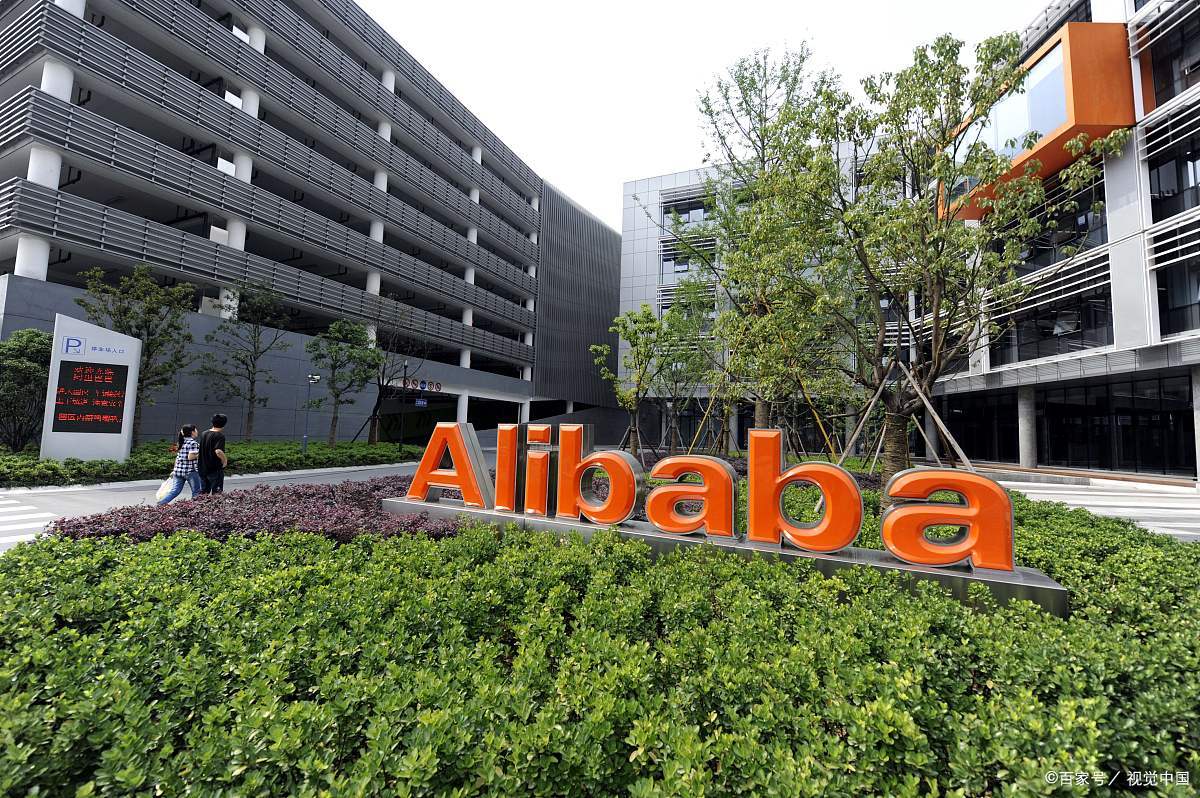
 博望財(cái)經(jīng)
博望財(cái)經(jīng)
 司庫財(cái)經(jīng)
司庫財(cái)經(jīng)
 投中網(wǎng)
投中網(wǎng)
 獵云網(wǎng)
獵云網(wǎ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