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人形機器人,已經開始倒閉了
人形機器人被視作“下一個萬億終端”,但2025年的賽道先傳來倒閉聲:硅谷明星K-Scale Labs燒光數萬美元后黯然關門,100多臺預購訂單被迫退款。
融資窗口收緊、供應鏈缺位,讓機器人“量產元年”看上去更像“生死元年”。
技術端,關節能耗、感知誤差與數據荒形成隱形天花板;成本端,40萬元BOM是馬斯克2萬美元目標的整整兩倍;場景端,工業產線狹窄、家庭付費意愿不足,ROI算不過來。資本市場開始區分PPT與現金流,誰能先突破性價比閾值,誰才有資格談“iPhone時刻”。
人形機器人,開始倒閉
K-Scale Labs,這家成立僅一年的類人機器人初創公司正在關閉。
該消息來自《The Information》看到的由CEO Ben Bolte發給投資者的一封郵件。
“公司目前剩余runway很有限,現金儲備大約為40萬美元。”他在郵件中寫道。Bolte表示,他原本預計很容易再融資1000萬到1500萬美元繼續推動公司發展,但融資嘗試失敗了。
該公司今年2月曾以5000萬美元估值完成約400萬美元的種子輪融資,領投方為風投機構Fellows Fund。今年4月,投資人Nat Friedman和Daniel Gross也向公司追加了25萬美元投資。
K-Scale開發了一款能夠雙腳行走、并使用開源軟件的類人機器人。來自OpenAI、Nvidia和Amazon等科技巨頭的員工曾到訪公司位于斯坦福大學附近的一處房屋,用于參觀其機器人研發現場。K-Scale擁有大約10名員工,但隨著資金耗盡,許多核心員工在過去數月已經離職。
Bolte在郵件中寫道,他曾與類人機器人公司1X Technologies的CEO Bernt B?rnich探討被收購的可能性,但B?rnich“明確表示他只考慮收購K-Scale的少數幾名團隊成員,而不會收購公司的其他資產。”Bolte還稱,他與另一家機器人公司The Bot Co.也進行過類似討論。1X發言人對此拒絕置評,The Bot Co.未回應置評請求。
Bolt同時在K-Scale的Discord社群中發布了說明,稱所有預購的機器人將無法交付,公司會退還訂金。根據一位前員工的說法,公司已經制造了10臺原型機,并獲得了超過100臺機器人的訂單。Bolte表示,OpenAI的機器人業務負責人Caitlin Kalinowski曾預購過其中一臺。每臺機器人的售價約為1.5萬美元,公司累計獲得了超過200萬美元的訂單。
K-Scale Labs是一家成立于2024年、總部位于硅谷帕洛阿爾托的類人機器人初創公司,由Benjamin Bolte等人創立,目標是以“開源、低成本、可被開發者使用”為核心理念,打造面向研究者和開發者的通用類人機器人平臺。公司嘗試從硬件到軟件全棧自研,既設計機器人本體、關節與驅動系統,也公開控制與仿真軟件,希望通過“仿真→真實(sim-to-real)”訓練路徑加速機器人學習能力落地。
其代表產品是一款可雙足行走、售價約1.5萬美元的全尺寸humanoid,曾引來來自OpenAI、Nvidia、Amazon等公司的工程師上門參觀,并吸引到Fellows Fund、Nat Friedman、Daniel Gross等知名投資人的種子輪投資,估值一度達到5000萬美元。然而,由于類人機器人硬件研發與量產本身對資本、供應鏈與工程人力的要求極高,公司在僅有約10人的情況下很難同時推進開發、迭代與規模化交付,融資進展不及預期,現金消耗迅速。盡管曾嘗試尋求1X Technologies等潛在收購方,但對方更傾向于直接吸納少量技術成員而非整體接盤。隨著核心人員陸續離開、現金儲備縮至約40萬美元,公司最終宣布關閉,并承諾退還預訂用戶的機器人訂金。這使K-Scale成為類人機器人賽道中一個典型的“技術有潛力、理念有吸引力,但在資金與工程體系尚未成熟前過早沖向量產”的失敗范例。
被量產難住的機器人
機器人產業正站在“量產元年”的門檻上,卻像被卡在最后一公里的快遞——看得見終點,卻遲遲送不到用戶手中。2025年全球人形機器人訂單量首次突破萬臺,資本市場歡呼“奇點已至”,但產業鏈上下游卻用財報和良率數據給這股熱情潑了一盆冰水:特斯拉Optimus把年度產能從5萬臺下調,資本與技術之間出現了一條“量產鴻溝”,它的深度由三件事決定:技術是否夠用、成本是否夠低、供應鏈是否夠穩。
在實驗室里,機器人可以后空翻、泡咖啡、寫毛筆字,但一旦進入產線,三大“隱形天花板”便暴露無遺。
首先是關節模組的能耗悖論。人形機器人動輒30—40個自由度,每個關節都需要輸出大扭矩,卻只能用低能效比的旋轉電機+減速器方案。業內測算,一臺50kg負載的機器人連續工作4小時,能耗高達2.3kWh,相當于一輛微型電動車跑20公里,而電池系統能量密度仍停留在250—300Wh/kg,無法突破“續航—重量—成本”的不可能三角。
其次是感知精度的“厘米級”誤差。工業場景要求重復定位精度≤0.02mm,但主流RGB-D相機在動態遮擋下的感知誤差>5cm,六維力傳感器分辨率僅0.1N,只有工業標準的十分之一,導致機器人在精密裝配環節“一抓就偏、一插就歪”。
最后是算法泛化性的“數據荒”。真實場景數據采集成本約50萬元/萬小時,虛擬仿真數據復用率卻<30%,每臺新場景機器人仍需12—18個月重新訓練,比工業機器人多出一倍時間,直接推高了小批量試產的技術風險溢價。
馬斯克曾斷言:“只有把成本壓到2—3萬美元,人形機器人才會迎來iPhone時刻。”但2025年行業平均BOM(物料清單)成本仍高達40萬元人民幣,是目標價位的兩倍,其中**執行系統占55%**。
核心零部件依賴進口是“罪魁禍首”。行星滾柱絲杠、諧波減速器、六維力傳感器三大件占關節成本70%,全球70%市場份額被日本哈默納科、德國ATI壟斷,進口單價萬元級,國產替代雖便宜三分之二,壽命與精度卻差一半,下游廠商不敢貿然切換。
非標準化生產進一步放大成本。機器人關節、傳感器接口缺乏統一協議,每家都要開定制模具,單套費用>50萬元,裝配時間比標準件長3倍;超精密加工依賴進口慢走絲機床,良率僅60%,比工業機器人低30個百分點,等于每生產100臺就有40臺要返工,隱性成本直線上升。
機器人產業尚未形成類似新能源汽車的Tier 1—Tier 3金字塔供應鏈,而是呈“倒三角”:頂層需求剛起量,底層百余家中小工廠分散在長三角、珠三角,各自生產齒輪、電機、減速器,缺少年產十萬級的大化工場。
關鍵部件產能全球占比上,中國行星滾柱絲杠、諧波減速器合計僅19%,日本占60%,且擴產周期長達24—36個月,與需求爆發期錯配。以2028年全球人形機器人需求10萬臺/年倒推,僅減速器一項就存在8萬臺的缺口,等于現有產能翻倍才能滿足。
原材料同樣受制于人。輕量化用的碳纖維國內自給率30%,高端鋪絲機被日、德實施出口管制;鈦合金粉末90%依賴進口,價格隨航空航天需求波動,導致機身減重方案遲遲降不了本。
即便解決技術與成本,機器人仍要面對“用得起”與“用得值”的終極拷問。
工業場景里,機械臂已覆蓋90%標準化工藝,人形機器人只在飛機檢修、戶外救援等狹窄空間才有“多自由度+移動”優勢,但全球年需求<1萬臺,無法支撐10萬臺級產線開滿產能。
家庭場景更尷尬。掃地機器人、智能音箱已以5000元、2000元價格錨定了用戶心智,人形機器人若售價>20萬元,卻只能完成擦桌子、取快遞等“癢點”功能,付費意愿僅10%—15%,遠低于智能音箱的40%。
ROI(投資回報率)過低讓首批客戶猶豫。以3C工廠為例,一臺人形機器人替代兩名工人,年節省人力成本14萬元,但設備折舊+維護費高達18萬元/年,等于“省的錢還不夠修機器”,投資回收期>5年,遠高于工業機械臂的1.5年。
當機器人從工廠走向客廳,數據隱私、事故責任、社會接受度成為新的“隱藏關卡”。
視覺、語音傳感器24小時采集環境數據,卻缺乏統一脫敏標準;一旦泄露,企業面臨《個人信息保護法》最高5000萬元罰款,但目前行業尚無本地化存儲與匿名化處理的成熟方案。
責任界定同樣模糊。機器人在家庭碰撞老人、在工廠誤操作損壞設備,算法開發者、整機廠商、終端用戶誰擔責?法律空白讓保險公司不敢出保單,企業只能自留風險,相當于每臺設備增加2%—3%的“保費等價成本”。
“恐怖谷效應”進一步拉低購買意愿。調查顯示,60%用戶對表情僵硬、動作機械的人形機器人產生心理抵觸,企業不得不投入額外研發資源做“擬人化”皮膚、柔性關節,卻再次推高成本。
機器人的未來
把機器人做成人形,最初像是科幻小說留下的包袱,卻在工程和商業世界里變成一條必須走到頭的路。兩條胳膊兩條腿的造型看似多余,實則是一張可以無限復用的“通用接口”。
人類用萬年時間把周遭環境修建成適合自己身體尺寸的樣子,門把手高一米、樓梯臺階十五厘米、流水線高九十厘米,所有這些沉默的標準都在等人形來對接。如果換成四足或者履帶,先得花大錢把廠房、廚房、商場全部改造,這筆賬算下來,遠不如直接復制一個人形外殼來得劃算。
更關鍵的是,人形提供了最高密度的“自由度性價比”。三十幾個關節就能覆蓋人類百分之九十的動作,拿螺絲刀、按電梯、開冰箱門都在同一套坐標系里完成,機械臂再靈巧也得換夾具,人形只要換手部末端,十分鐘內從擰螺絲切到端咖啡,產線切換成本趨近于零。
這讓“一款機型打天下”的商業模式第一次有了可行性,也是資本愿意忍受當下四十萬成本的最大理由——規模上來后,每多賣一萬臺,研發費就被多稀釋一次,邊際成本曲線比任何非標自動化設備都陡峭。人形還是“交互入口”的最優解。心理學上有個“恐怖谷”,但更有“移情峰”,當機器外形足夠像人又保留恰到好處的機器感,用戶會在潛意識里把它當成社會成員,愿意開口說話、分享情緒,甚至托付老人小孩。
酒店前臺、醫院導診、展廳講解這些崗位賣的不只是動作,更是溫度,一張笑臉、一個揮手就能把客戶留存率提升十個百分點,換成圓盤底盤加升降柱就徹底失去魔力。反過來,數據也證明人形能把客單價撐住:同樣遞送一杯咖啡,履帶底盤只能收兩元服務費,人形可以掛出“咖啡師”牌子收五元,用戶還愿意拍照發朋友圈,流量價值再返還給品牌,ROI模型立刻好看得多。場景方面,最先跑通的一定是“夜班補位”和“有毒工序”。新能源汽車電池車間要二十四小時恒溫恒濕,人類夜班效率低、事故率高,人形機器人不需要照明,也不會吸入化學蒸汽,兩年就能回本。
商場擦玻璃、加油站值班、燒烤店翻臺,這些崗位招人難、流動大,人形機器人不用交五險一金,也不會中暑,每天十六小時兩班倒,老板把省下的工資拿去還設備貸,賬算得明明白白。家庭場景看似遙遠,卻可能后來者居上。
貴州山區用機器人背茶青,一趟四十公斤,兩小時走六公里,把鮮葉下山時間從傍晚提前到中午,賣價每斤多收五元;東北滑雪場租給人形“跟拍攝影師”,時速六十公里滑下山,自動追拍并實時剪輯,游客愿為三十秒短視頻付九十九元,節假日一臺機器日流水三千元,三個月回本。甚至連殯葬業都在詢價,人形機器人穿黑西裝、捧骨灰盒,步伐穩重、表情肅穆,比雇人更可控,也免去了“忌諱”心理帶來的招工難。所有場景的共同點是“人機接口無需改造”,人形只要學會動作就能上崗,這才是它不可替代的底層邏輯。當成本曲線再下移一次,十萬關卡被擊穿,這些散點需求就會連成一片...
人形機器人不再只是“長得像人”,而是真正變成社會的“通用勞動力”,把人類從重復、危險、不體面的工作中解放出來,去從事更創造、更溫暖、更有趣的事。到那一天,人形不再是科幻包袱,而是商業世界最理所當然的形狀。
猜你喜歡
臥安機器人沖刺IPO:李澤湘的非人形賭局,增收不增利何解?
這家由“大疆教父”李澤湘孵化的深圳企業,正試圖改寫資本市場對機器人行業的認知。



 融中財經
融中財經
 獵云網
獵云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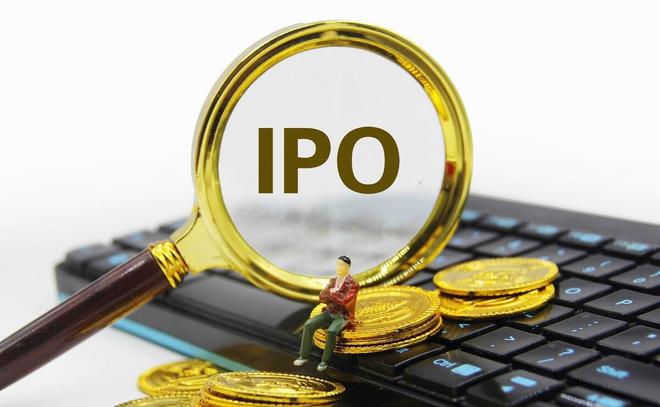
 東四十條資本
東四十條資本
 博望財經
博望財經




